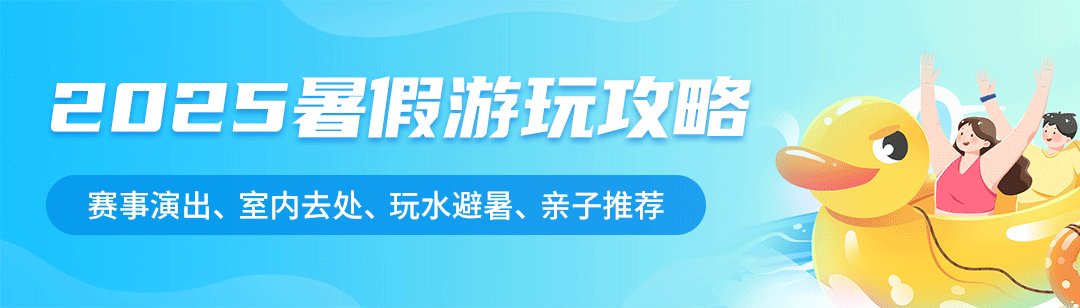北京通州历史:因漕运而兴的京师屏障(图)
导语 从金代开始,“坐拥”大运河的古城潞县(今潞城镇)就备受历代统治者的关注,渐渐的,因希望“漕运通畅”而有了通州。通州从此也因漕运而兴盛。
从金代开始,“坐拥”大运河的古城潞县(今潞城镇)就备受历代统治者的关注,渐渐的,因希望“漕运通畅”而有了通州。
此图为《潞河督运图卷》局部,清代江萱画。这幅画描绘的是乾隆时期运送南方各省漕粮抵达通州时的繁忙景象,但也有学者指出此画反映的是天津三岔口漕运景象。
通州从此也因漕运而兴盛。元代,修建通惠河运送粮食;明清时期,除了通惠河,还通过陆路运送粮食,通州被称为“皇家码头”,扼守北京城的东大门。当然,更多的漕粮及货物都被暂存在通州,因此,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物资都汇集于此,形成了货品丰富、琳琅满目的繁华市集。清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他们一路沿着运河北上,在通州上岸进京。他们目睹了通州作为“天下第一通漕之处”的繁盛景象。
如今,虽然漕运不再兴盛,但通州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再次成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节点之一,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将再次矗立于古运河畔。
西汉
先有潞城后有通州
地铁6号线的东端首站潞城是未来行政副中心的核心所在地。很多人们会有些奇怪:说是“城”,但是为什么没有见到城呢?在历史上,“潞城”确实是一座古城的名称,其故址就在潞城镇政府西侧的古城村。
西汉初年,涿郡(今北京)的东面设置了一座城镇,由于这座城正好位于东西往来的通衢要道上,因此便以“路”字命名,取名为“路县”。其所辖范围除了今天的通州区以外还包括河北省三河市大部分地区以及平谷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当时的燕郊和通州属于路县。后来由于县城西侧有一条叫做“潞水”的河流(即今温榆河),因此而改名为“潞县”。到了东汉初年,位于今天密云境内的渔阳郡将郡治迁到了这里,此后不久,郡守彭宠因为叛变而遭讨伐,整个潞县城在兵火中化为灰烬。重新设置的潞县迁到了今天燕郊东北的军下村(大致在规划中地铁平谷线三河西站附近)。到了北齐年间,潞县再次迁移,最终落在了今天通州城区的位置。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将隋朝的涿郡(即今北京)改名为幽州,第二年将潞县改名为玄州。幽和玄两个字都代表的是“北方”。同年,原属于潞县的东部地区单独设置为临泃县,这就是今天河北省三河市的前身。贞观元年(627年),废除玄州,重新改称“潞县”,临泃县也在开元四年(716年)改名为三河县,并隶属于幽州。这是通州和三河的第一次“分手”。
五代的后晋时期,北方幽云十六州被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给了辽国,后来金灭辽,将幽州升格为中都城。为满足都城粮食的供应,位于大运河北端的潞县受到关注。因为来自于南方的粮草,大多要通过运河到达潞县,再运抵都城。于是在金朝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正式将这里命名为“通州”,取“漕运畅通”的含义。这也是通州命名之始。
元朝
通惠河将南方粮食运进城
元朝废弃了原金中都城池,在其东北另筑新城,即如今的元大都城。在兴建新都的同时,还开展了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即修整大都城到通州的运河,以便利漕运。当时为了南方的粮草能够顺利运抵大都,分别疏浚了三条运河。位于中间的这条河,起点在元大都城中的积水潭(即什刹海),向东流经万宁桥(即后门桥),沿着皇城东萧墙一路向南(即今南河沿大街一线),从文明门(今东单路口)西侧的水关出城后折向东,直抵都城东面的通州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漕运干线——“通惠河”。
与通惠河同时疏浚的还有两条河流,一北一南与通惠河互为呼应。其中位于北面的这条河流至今仍存,望京地区的一条重要的街道名称也源于此河,这就是元代都城漕运的北线——阜通河。此河同样源自于积水潭,之后沿着今天北二环一线向东,由大都东北门光熙门附近水关出城,最后向东注入北运河的上游温榆河。这条河流和它的支流为我们今天留下了亮马桥、酒仙桥、西坝河、东坝、三岔河等地名。通过这条运河,南方的粮草还可以走北线最终到达都城内的积水潭。这条河流经一座水坝,名为“郑村坝”,即今天的东坝村。明朝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和建文帝的中央军在这里有过一场激战,燕王采纳了手下宦官马三宝的意见,最终取得了胜利。兴奋之余便用郑村坝这个村名给马三宝改姓为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下西洋的郑和。
位于南面的这条河流历史上也称为“萧太后河”,因在辽国萧太后的主持下兴建而得名。疏浚后的萧太后河也被称为“文明河”,因其源自于大都东南门文明门附近。如今这条运河位于城区的部分大多已经改为地下暗沟或者消失。不过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东城三里河以及朝阳区十里河的地名。保留在地面上的萧太后河西起西大望南路附近的双龙小区南侧,流经东南四环小武基桥后不久折而向东,最后注入北运河,这也是元代漕运的南线。
这三条运河的修筑,大大方便了南方运来的粮食运抵都城的速度和效率。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通惠河作为京杭大运河重要的组成部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明朝
通州的富庶震惊朝鲜使臣
明朝初年,通州的城墙改为砖筑,辟四门:东门通运门(6号线通运门站即由此得名),西门朝天门,南门迎薰门,北门凝翠门。明朝迁都北京后,加大了对于通州的重视程度。当时归属通州直接管辖的就有四个县,分别是漷县、三河县、香河县和武清县。直到清代雍正年间,为了让通州的职能更加专注于漕运和粮食仓储,才又将通州降格为“散州”,原其下统领的三河、武清、香河三县归属顺天府直辖。这是通州与三河县的第二次“分手”。
明代将通惠河在原皇城东墙外的部分圈入了皇城城墙内,并且将元大都的南城墙向南扩展,从而将通惠河沿着大都南城墙的一段河道整体圈入新的都城内而改为地下暗河。这就使得原有的通惠河从今天东便门附近“断流”了,再加上多年未进行疏浚,形成了较为严重的淤塞现象。因此很多运粮的商队开始选择陆路将粮食从通州运往京城,在京城东大门朝阳门内便形成了大量的粮仓聚集区。时至今日仍有南新仓、北新仓、禄米仓等地名遗存。
这条运粮的官道,也逐渐成为北京东部的重要交通要道。而对于每年都借道我国东北地区进入都城的朝鲜使臣,通州也成了他们的必经之地。
在这些朝鲜使臣的笔下,我们能够领略到当年通州的风采:“余见辽东人民物贸之盛,以为忧无比,比及到山海关,则辽东真如河伯之秋水,以为天下殷富此为无敌。今见通州,则山海关又不啻山店贫村。”这些使者们走出国门,来到我国辽东地区时,感觉这里和他们自己的国家比起来,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小康社会了,而到了山海关,则感觉辽东又成了小巫见大巫了。而将山海关和通州的繁华程度比较起来,山海关简直成了山村野店,不值得一提,足以见当年通州的富庶。
有趣的是,他们在这里还看到了明朝的帝王们为自己准备的“后路”:“上自皇上,下至百僚,计员有船。脱有缓急,各乘此船直达金陵之计也。”也就是说,在通州的运河上,昔日确实停靠着龙船和其他一些大型船只,而其用意即是朝鲜使者所记录的那样,在危急时刻供皇帝和百官“跑路”用。
由于漕运的繁忙,当时的通州的确达到了盛极一时的状况。每年阴历的三月初一,北直隶、河南和山东诸省的运粮船便沿着运河抵达通州了,这之后四月安徽,五月南直隶,六月浙江、湖广,一直延续到十月,各省区的船帮按照规定的日子陆续抵达,每一支船帮按规定只能在通州逗留十天,由于时间短,卸货任务重,就直接导致了通州城“城门夜不闭,灯火烂星光”的繁忙景象的出现。
东便门外大通桥,当年漕运的终点
通州的古城门 清朝 修建宽17米的“京通快速路”
到了清朝,通州仍然发挥着漕运和陆路运输枢纽的作用。为了提高陆路运粮的效率,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决定修筑一条由朝阳门到通州的石板路,来加快运粮的速度。在《御制通州石道碑》中雍正皇帝谈到了修筑这条石板路的重要性:“自朝阳门至通州四十里为国东门孔道……由通州达京师者,悉遵是路。”同时他也讲到了运河在漕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每年大量的粮食到京,在通过陆路运往京城的过程中,不免会对原有的土路路基有所破坏,很多地方出现了地势低洼的境况,尤其是赶上夏天降雨或者是冬日里积雪融化的日子,车轮往往会陷入到泥淖中难以前行。一辆车陷在那里了,就得需要数十人把它牵引出来,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所以朝廷最终决定修筑这条道路。
整条道路共长五千五百八十八丈多,宽二丈,换成今天的计量单位,就是道路总长19公里,路宽近7米。除此之外,在主干道两侧还有“辅路”,即重新对原有的土路进行了修整,每一侧的辅路各宽约5米,这样算来这条“高速公路”总宽度为17米左右,在当时来讲算是相当宽的大道了。
这条道路共建设了十个月,在主体工程以外还有配套工程,即将通州城内各仓库周边以及沿运河周边的土路全部改筑为石路,以加快粮草的运送速度。
另外,清代的北京周边还有两条类似的快速路,分别是供南方诸省人民陆路进京专用的卢沟桥到广安门石板路,以及供清代帝王们前往西郊园林避暑的西直门至圆明园的石板路。如今前者已经成为京港澳高速路的一部分,而后者则几经改道,最终融入了西北部城区重要的城市干道体系。